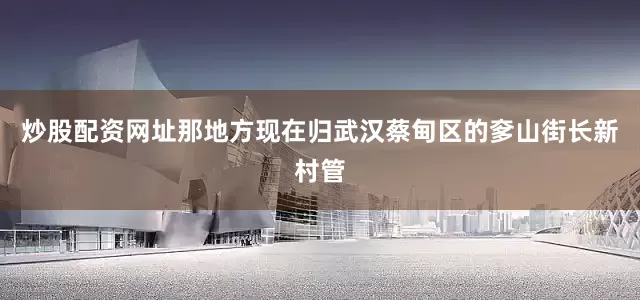
土地革命那会儿,鄂豫皖苏区是顶重要的革命地盘之一,那里的队伍后来发展成了红四方面军,这可是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。红四方面军最牛的时候,手下有八万精兵,啥硬仗、恶仗、险仗都不怕,打了一场又一场。这支队伍里,出现了好多勇猛善战的将领,等到新中国成立后,那些闪闪发光的开国将帅里头,有七百多人都是从红四方面军出来的。红四方面军能变得这么强大,成为一支铁打的队伍,早期红军的高级指挥员、当过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的陈昌浩可是功不可没。

陈昌浩,小名叫子藩,本名叫陈海泉,还有个曾用名叫苍木,他是1905年10月16日在湖北汉阳县的永安堡戴家庄出生的,那地方现在归武汉蔡甸区的奓山街长新村管。他爸叫陈荣发,号春霆,在汉口商行当领导,他妈叫吴蓉,主要负责在家料理家务。他们夫妇一共生了四个娃,两个儿子两个女儿,陈昌浩是老大。因为家里条件还不错,他小时候就被送到私塾念书了,那时候起他就叫昌浩了,接受的教育也挺严格的。这孩子聪明还努力,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,成绩都是顶尖的。在大学那会儿,他认识了一些思想进步的朋友,后来加入了组织,还被派到苏联去留学,成了当时特别有名的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”中的一员。

陈昌浩留学归来后,组织安排他到鄂豫皖根据地干活。在部队里,他因为勇敢果断,管理军队严格,特别是在指挥反“三路围攻”和反“六路围攻”这些大战时,展现出了非凡的指挥本事。靠着出色的军事领导能力,他很快在红军里出了名。那时候,红军打仗时抓到了一架国民党的飞机。身为领导的他,亲自押着被俘的国民党飞行员,揣着手枪和手榴弹,坐着飞机到了黄安城上空。他给敌军阵地扔传单、炸炸弹,给红军长了大脸。这事儿在红四方面军里炸了锅,大家都对他赞不绝口。所以,25岁的他就当上了方面军的总政委。

陈昌浩领导红四方面军那会儿,红军队伍是一天比一天壮大。特别是当他们挺进川北,那气势,简直了,人数直接飙到了八万多。每次行军,陈总政委都会穿上从川军将领那儿缴来的斗篷,外面是黑的,里头是红的,骑在马上随着马背起伏,威风凛凛,跟只展翅的雄鹰似的,冲在最前头,引得路人都停下来看。听警卫员后来讲,那时候的陈总政委,个子高挑,模样帅气,年纪轻轻的,不光是气势不凡的大英雄,还是个难得一见的美男子。要是把香港的大明星周润发换上红军装,披上将军斗篷,那模样,简直就跟年轻时的陈总政委一模一样。

打仗厉害,指挥得当,还年轻有为,在那个大家都崇拜英雄的战争时候,他的一举一动都特别吸引眼球。那时候,红军队伍和根据地的老百姓,都把他这位总政委看得跟神仙一样,他的故事到现在还在当地传着呢。听说他手下有个军长,战功不少,可就是脾气太坏,做事霸道,谁要是跟他顶嘴,他就拿枪吓唬人,“砰砰”几声子弹打在地上,吓得人魂飞魄散。没想到这事儿让总政委陈昌浩知道了,他立马带着警卫员跑到军长那儿,抄起马鞭子就是一顿猛抽。军长吓得赶紧求饶:“总政委,我错了,我真的错了,以后再也不敢了。”这才算完。

但到了1936年11月,这位曾带领大军在战场上英勇奋战、立下无数战功的年轻红军将领,人生轨迹有了大变。那时候,上面决定成立红军西路军,要渡过黄河去,打通到新疆的路。陈昌浩被选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,还有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,带着队伍往西走,过黄河去打仗。接下来的半年,西路军被西北的军阀追得到处跑,最后在河西走廊吃了大败仗,红军历史上这事挺惨的,原本二万多人的队伍,最后只剩几千人了。到了这生死存亡的关头,陈昌浩最后一次以头头的身份,召集大家开了个急会,定了三条路子:第一,剩下的部队得散开打游击,继续斗;第二,两位高层得离开队伍,回陕北报告情况;第三,选工委领导来管各支队的行动。从这以后,他就正式告别了这支一起摸爬滚打多年的队伍和兄弟们。

那时候,“天空高远,大地辽阔”,1937年春天,陈昌浩离开了队伍,开始往东走。因为敌人太多,他们只能白天躲起来,晚上赶路,边战斗边前进。当他们走到一个叫大马营子的村子时,陈昌浩病倒了,烧得很厉害,被困在了西北荒原上的一个小村子里,那是湖北人但复三的家。他拿出自己身上一半的银元,分给了三个卫士,让他们各自逃生,然后又给了但复三十块大洋。但复三虽然只是个村里的土医生,但他是个有胆量、讲义气的人。看到陈昌浩病还没好却坚持要走,他就提出亲自送他回老家。陈昌浩把枪埋了起来,换上了但复三给他的便装,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,总算是回到了阔别近十年的老家——长新村。

在河西走廊的战役失利后,红西路军的悲壮故事里,一万多名红军战士牺牲了宝贵生命,书写了英勇无畏的篇章。作为领头人的陈昌浩,看着自己带的队伍吃了大败仗,心里头那个痛啊,真是无法形容。他满心愧疚和自责,回到延安后,不管在哪提到这事,都痛心地说:“祁连山那一败,我陈昌浩真是有责任,一万多兄弟,命丧大漠……一想到那些倒在荒野的战友,我就心如刀绞。”之后,他就离开了部队,经过组织同意,陈昌浩去苏联治病了。1939年8月27日,陈昌浩搭乘飞机,离开了这片他战斗了近十年的土地,前往苏联。飞机上天,他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,心里头思绪万千,不知道到了苏联会面对啥样的境况……

陈昌浩刚到这儿养病时,比起国内战火纷飞的情况,莫斯科的医疗和生活条件都要好得多,吃的用的都挺丰富。他儿子陈祖涛记得,刚到莫斯科那会儿,跟延安的苦日子比起来,“那儿的日子简直跟仙境似的”。他们每天都能吃上白面包、奶油,还有各种水果,这对之前在延安靠小米填肚子的陈祖涛他们来说,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福气。在这儿,陈昌浩得到了精心的照料,医生隔三差五就来给他查体,积极治疗,没多久,他的老毛病就快好利索了。

真没想到,好景不长,紧接着苏德战争就打响了,陈昌浩的命运再次遭遇坎坷。那时候,战事紧得要命,那些原本支援我们的福利机构也被迫关门,所有人都得赶紧撤到后方去。逃难的人多得跟潮水一样,到处乱窜。他就跟着一大帮人,被安顿到了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,靠近塔什干的一个小镇,叫科坎加。

塔什干这个名字在乌兹别克语里头的意思就是“石头堆成的城”,为啥这么叫呢?因为它坐落在山脚下的冲击平原上,那儿有好多大石头。这地方位于中亚的正中央,太阳一晒,沙子就跟海浪似的翻滚,所以大家都叫它“荒漠之地”。正因为这样,水在这儿就成了个宝贝。咱们中国古代有好几位探险家,像张骞、法显、玄奘,他们都到过这儿。特别是张骞,书上说,汉武帝派他到西边儿出使,他就走到了塔什干。在那儿,他还成了家,有了孩子。后来张骞回了汉朝,可他的妻子和孩子被匈奴给抓走了。他想派人去救,但遗憾的是,一直都没能找到他们。

陈昌浩来到这儿安顿下来后,碰上苏联那边把以前的组织给解散了,他的所有供给就都断了。他以前可是个军人,还是个级别不低的指挥官,做饭、洗衣服这些他从没干过,买东西砍价更是一窍不通。所以,他得自己想办法过日子了。在这儿,大伙儿压根不知道他以前是红军里的大人物。

为了活下去,他跑到科坎加那地方的采石场干苦力活。那边不仅有采石场,还有榨油厂这些工厂。一开始,陈昌浩就在采石场打工赚钱,天天砸石头、扛石头,就为了养活自己。尽管他从早到晚都在卖力干活,但因为那时候战乱,东西特别少,就算这样,他每天也只能分到一斤左右的黑面包,还有一点点土豆,吃的非常少。

在采石场干活,那可不是一般的累。就像老辈人诗里写的那样,“云阳路上走一遭,两岸都是做买卖的。热得像吴地的牛喘月,拉船拉得那叫一个苦!河水浑得没法喝,水壶里的水半拉都是泥。一唱起那都护歌,心里头难过得眼泪直淌。成千上万的人绑在石头上,没法到河边去。你看看那满山的石头,想想都让人掉眼泪。”苦的时候,大家也会找点乐子,哼几句采石歌,“离了破草屋,进了山里头,还不是因为没钱又过不上好日子。天天采石头,这活儿也不顶用,真是恨自己没能耐,遇不上贵人拉我一把,就不用受这穷罪了。”……从这些歌里,你就能看出他们对过好日子的盼望。

陈昌浩因为长时间辛苦采石,又老是饿肚子,原本高大健壮的身体被病痛、饥饿和重活给拖垮了,变得特别虚弱。再加上那儿的气候实在太差,一会儿冷得要命,一会儿又热得不行,让他的胃病老是犯,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。采石场边上有个榨油的地方,那些一起干活的苏联工人看陈昌浩这个外国人挺可怜的,有个老工人就跟他说,去榨油厂喝点热棉籽油,胃病能好。他还真去了,喝了几回,没想到,多年的老胃病竟然就这么好了,再也不疼了。这事儿,还真是倒霉中的万幸。他心里头那个乐啊,别提多高兴了。

陈昌浩在搬运和采石的工作岗位上干了两年,那时候,他差不多天天都给那些以前熟识的苏联朋友们写信求助。但因为仗打得紧,大部分信都像丢进大海的石子,连个泡都没冒。但坚持总会有回报,终于有一封信被之前和他共事过的季米特洛夫看到了,这一下子,他的命运有了大转弯,不用再在那个荒凉的采石场待到老了。之后,季米特洛夫决定让他去前线当翻译。他立马换上了军装,直奔斯大林格勒前线,主要负责把公函翻译出来,履行了一个国际主义战士的责任,后来还赢得了一枚“卫国战争奖章”。


在这段时间里,让陈昌浩感到高兴的是,有个朋友帮他认识了一位俄国的姑娘,名叫格兰娜。她一瞧见他,见他身材高大、长相帅气,对人亲切,俄语说得还特别溜,立马就被他的魅力给吸引住了。打那以后,她心里就对他有了好感,决定要好好照顾他的日常,好让他能专心翻译和写作。到了1945年5月1日,他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,生了个娃,小名叫维克多,意思是胜利,大名则叫陈祖莫,意思是莫斯科出生的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经过上面的点头,陈昌浩带着老婆孩子,眼里含着泪,回到了阔别十三年的老家。从莫斯科走的时候,他别提多高兴了,紧紧抓着来送行的人的手,激动地说:“咱们终于能回去了!”说着说着,他居然大哭起来,眼泪跟下雨似的。十三年啊,盼了十三年!这回终于能回自己的国家了!到家后,他当上了编译局的副局长。到了1967年,他快不行了,给儿子和家里人写了首诗,算是对自己这一辈子的总结:心里有大义,一心要报国,不想留名世,只愿当基石。
北京炒股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